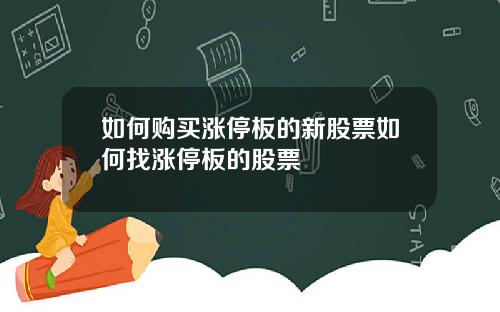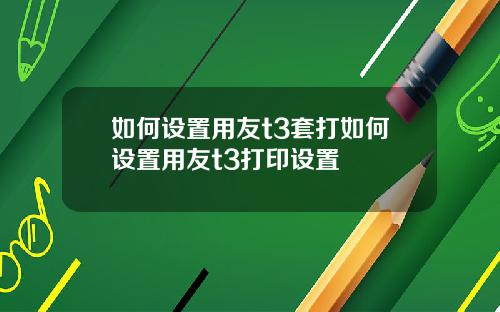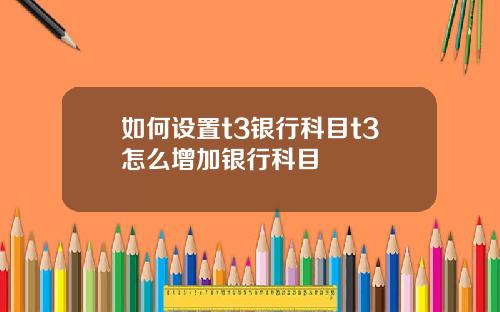石门湾,千里运河第一湾
文 | 颜伟光
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的石门镇,京杭大运河在这里拐了120度的湾,一座吴越疆界碑诠释了石门名称的由来,一位文化巨匠倾诉了他的柔柔乡情,一个距今7000多年的遗址,因座落在石门镇的罗家角村而得名,历史在石门镇有着太多精彩的传奇色彩。
一、千里运河第一湾
2019年新春佳节,我从嘉兴市区出发,沿着桐乡大道至桐乡市,再向西行约7公里就到达了石门镇。我站在石门大桥上远眺,阳光下的石门湾犹如一个大大的港湾,几十条巨大的铁壳船静静地停泊在开阔的石门湾里。走近石门湾,京杭大运河在这里波澜不惊地流过,偶尔能见到有船只过往。岸边开着些商店,整条小街尽显江南水乡特色。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向北流经崇德、再向北流到古镇石门镇时,在寺弄口来了个120度的大转弯,折向东流去。因为运河形弯如玉带,所以这里也叫石门湾、石湾、玉湾、玉溪。石门湾是千里古运河上第一湾。
据记载,隋修运河,唐朝初在石门设水陆驿站,称石门驿。宋熙宁十年,也就是公元107年,石门镇划归崇德县。嘉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208年置石门乡。元、明年间,石门镇市混用。明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1430年,崇德县分六乡建桐乡县,石门分属崇德、桐乡两县,以接待寺为界,寺东属桐乡,寺西属崇德。清康熙元年,也就是1662年,改崇德县名为石门,石门镇遂改名玉溪镇。民国3年,也就是公元1914年,石门县恢复崇德县名,玉溪镇复称石湾镇。
石门镇为历代浙北要冲之地,大运河自南而来经镇寺弄口折东,湾形如玉带,同时可通百舟。运河上通福建、广东,下达上海、江苏,成为南北交通要道。历经唐宋元明清,贡赋漕运,迎来送往,从没停止过。直到今天,交通运输有了更为快捷、更为现代的方式。但在石门湾,千年运河依然在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
从唐朝开始就在石门设置驿站,后来的历朝历代,都在石门设置重要驿站。不仅驿使往来于此不绝,就是“官舫贾舶皆泊于此”。贡赋漕运,来往货物船队,到了石门湾这个地方,都习惯地停下来歇歇脚,整顿整顿精神再上路。当年这里,舟车驿马,昼夜不绝,灯火明灭,人声鼎沸,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宋室南渡后,康王赵构车驾常往还于石门道中,石门成为其驻跸之所。绍兴中,也就是公元1626年,于石门驿基建行幄殿,即皇家行宫。
乾隆年间,也就是公元1736—1795年,乾隆多次南巡江南,沿运河至嘉兴、杭州,中途夜宿石门,就是从石门湾上岸的。今石门有地名“营盘头”,传为乾隆六下江南夜宿处。1757年,乾隆经过石门时,写下《过石门诗》,“策马石门县,官民度石城”。
因为运河,到了明清两朝,石门湾商贸之发达在县城之上。石门镇成为了江南著名的桑市。据清康熙《石门县志》卷二所记,石门有晚青桑等十二种桑树。明王樨登《石门曲》:“采桑复采桑,蚕长桑叶齐,妾住石门东,郎住石门西,卖丝家复贫,哭解红罗襦。”到清代,各地都买石门桑种来种植。张燕昌《鸳鸯湖棹歌》:“侬家接得石门种,十亩闲闲蔽草堂。”该书自注:“桑以石门种为美,吾乡(秀水)桑种,多接枝叶尤茂。”施钟成《玉溪杂咏》云:“石门叶市甲于禾郡。”桑市规模超过当时的府城嘉兴。
明清间,石门镇还成为了棉布茧丝的重要产地。《玉溪杂咏》云:“织成片段赛丁娘,四手戈不研光。昨日金陵标信到,客帮都道要东庄。”朱彝尊也诗云:“五月新丝满市廛,缫丝鸣彻斗门边,沿流直下羔羊堰,双橹迎来贩客船。” 与此相应,石门丝绸、棉布业交易也很发达,至今,在缘缘堂边上还有“棉纱弄”这样的地名景
石门镇还是粮食集散地。明代崇德县因盛植蚕桑占了粮田,每年缺四个月的粮食,其粮食则靠运河从长江中游的湖广、安徽等地贩销。石门则是崇德县的第一个市镇,镇上布满了粮店,生意十分兴隆。
明清时,石门镇还成为浙北规模最大的榨油专业市镇。榨油业以外地输入大豆为原料,凭借的就是大运河便利的交通优势,大量的大豆通过运河输入江南,运销到石门,使石门成为江南规模最大的油坊。到清末民初时石门镇及附近至少有25家油坊,无论是大豆原料,还是油和油饼都已经打破了狭小的区域市场,成为浙北乃至江南的榨油基地或生产中心。
然而,经过一次次战乱,特别是抗日战争,石门频繁遭受几次轰炸和炮击,全镇几乎尽毁无余,瓦砾遍地,经济衰退。直到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恢复发展。
二、吴越争霸垒石弄
在石门,这里曾经旌旗猎猎,战火雄雄。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石门成为主战场之一。刀与火,剑与矛,血与泪,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寻找疗治秘籍。垒石为门,以为界限,故此地得名石门。如今,地名与界碑尚存,砖墙相对的“垒石弄”,以断壁残垣的姿态展示曾经的故我,供人怀古思旧。
据记载,石门这片肥沃而平坦的土地有着7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但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它是以一个开天辟地般的大事件拉开序幕的,这个大事件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越争战”。《春秋》有十二个字记录下了这一大事:“定公十四年,於越败吴于槜李。”“定公十四年”就是公元前496年,而“槜李”就是现在的桐乡包括石门一带。
吴越两国争战,桐乡这一带自然就成了两军对垒厮杀的主战场,你退我进绞着拉锯的区域。血雨腥风的战争给桐乡这一片当时原始得还如同一张白纸的旷野上涂抹上了一层战火的色彩,石门、垒石弄等一个个地名,蕴含着几分战争的痕迹,也透露着几分血腥和野蛮,聚敛了千军万马的气势,铸就了铜墙铁壁的坚固。
石门之名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吴越争战的产物。“尝垒石为门,为吴越两国之限”,兵锋既起,车马相逐,双方遂筑城划疆而治。越王在此垒石为门以防吴,吴王亦结寨屯兵于此以拒越,森严壁垒,针锋相对,俨然一派一触即发的态势,弥漫着浓重的战争气氛。
如果说石门是吴越两国的边界,那么垒石弄就是边界的中心线,它处在镇中间,南北向,长不过百米,宽仅3尺,人们倚门而立,可侃侃而谈,也可窃窃私语,亲昵如同一家人。但在那时,却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的两国。
垒石为门,结寨屯兵,当时是战争的需要,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到后代,风烟散尽,遗迹依稀,便成了文人雅士怀古思远的最好来由。“人事有代谢,往事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好古是风雅之士的共性。在石门,也留下了许多凭吊遗迹的诗篇。
明代时,嘉兴知府钱荣曾写过一首诗:“苍茫白石锁寒塘,十里尘埋古战场。人物已非天自老,山河依旧世空忙。千年迹在湾流碧,一代兵销草木长。几度登临陪惆怅,西风吹泪洒荒凉。”清代郑镰有《玉湾怀古》诗:“春秋尚争地,吴越此分土。可怜一夫差,属镂杀良辅。不顾抉眼臣,遂亡伤指父。有仇不能报,此恨成千古。”
在清代,“石门故垒”还被列为“桐溪八景”之一。邑人陈润的《石门故垒》写得最精彩:“古塞千年尚有基,断横残石草离离。风烟不散英雄气,犹如吴兵百战时。” 1991年当地政府在垒石弄南首,运河岸边,竖起一碑,上书:“古吴越疆界”,作为追溯石门历史源头的一个标志。
三、丰子恺故居
石门镇的后河上有一座桥,叫木场桥,只见石桥栏上镌刻着多幅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从木场桥下来,向南转弯,来到绵纱弄,绵纱弄西首有一幢坐北朝南的宅院,这便是现代著名画家、文学家、美术音乐教育家丰子恺的故居缘缘堂。
丰子恺1898年出生在石门镇,是我国著名的现代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早年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1921年去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浙江、重庆等地从事美术和音乐教学。漫画受日本竹久梦二影响,作品清新、朴实。有作品集《护生画集〉、《音乐人门》、《缘缘堂随笔》等。
丰子恺生前到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地,他总要因陋就简地建设一个宁静而温馨的家,并为这个家园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比如“小杨柳屋”、 “缘缘堂”、 “日月楼”。 而“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的现实家园,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不仅几次撰文描述缘缘堂,还将自己的文章一再以缘缘堂的名义结集出版,如《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和《缘缘堂续笔》。
最初的“缘缘堂”是丰子恺在上海江湾永义里的一个宿舍,当时他正在立达学院教书。1927年初秋,丰子恺的恩师弘一法师来到上海,住在他家里。丰子恺就要求恩师为他的寓所起名,弘一法师让他在小方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阉。结果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就取名为“缘缘堂”。
1933年春天,丰子恺用积攒起来的稿费,在故乡桐乡县石门湾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的后面建造了一幢三开间的高楼。这就是真正的缘缘堂。丰子恺十分喜欢这幢自己设计的纯中国式的小楼,高大轩敞,明爽简洁,具有朴素深沉之美,并认为它“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他用一块数十年陈旧的银杏板雕刻缘缘堂匾额;请弘一法师把《大智度论?十喻赞》写成一堂大屏,装裱后挂在匾额的两旁;匾额下面,是一幅吴昌硕画的老梅中堂;中堂两旁又是弘一法师书写的一副大对联:“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大对联旁边又挂上他自己写的小对联,用的是杜甫筑成草堂时表达欣喜之情的诗句“暂止飞乌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十分贴切地吻合了丰子恺当时的心情。
在配置家具等其他物件时,同样非常注意全体的调和。在一篇文葶中,丰子恺这样描述对缘缘堂的赋形:“因为你处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所以我不给你穿洋装,而给你穿最合理的中国装,使你与坏境调和。亲绘图样,请木工特制最合理的中国式家具’使你内外完全调和。”
丰子恺还很注意布置周围的环境,在院子里种满了许多花丼,如樱桃、蔷薇、芭蕉、葡萄、凤仙、鸡冠、牵牛、柳树等,无论春夏秋冬,都能闻到花的清香,欣赏大自然赋予的丰富色彩。
然而不幸竟是接踵而至,上海江湾的缘缘堂于1932年毁于日军的炮火,石门湾的缘缘堂又于1938年初在日寇进犯浙江的炮火中化为灰烬。这不堪回首的一幕令丰子恺无比伤心和愤怒。他接连写了《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和《辞缘缘堂》三篇文章,向残暴的日军发出了复仇的宣言。同时相信,当暴敌被歼,中华民族重新获得和平以后,绾缘必定会复活的,“我们不久一定团聚,更光荣的团聚”。
1985年9月15日,在丰子恺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在丰子恺生前挚友广洽法师的资助下,由浙江省桐乡县人民政府重建的先生故居缘缘堂正式落成,广洽法师专程从新加坡赶来主持典礼,丰子恺生前友好和艺术界人士聚会石门湾,场面隆重热烈。
丰子恺在上海寓居“日月楼”的21年中,勤于笔耕,写作,翻译,成果累累。他翻译了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等。与幼女合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第1至4卷。创作了《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等散文。出版了《丰子恺儿童漫画》、《子恺漫画选》。完成了《护生画集》第4、5、6卷的绘画工作,使这一桩他与恩师弘一法师共同发起的护生宏愿在漫长的40多年中得以善始善终。
在丰子恺先生眼里,石门湾的繁盛,早已超过了县城,他回忆石门湾时曾描述 “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麋集在这湾里,等候你去雇。” “你如果想通过最热闹的寺弄,必须与人摩肩接踵,又难免被人踏脱鞋子。因此石门湾有一句专业的俗语,形容拥挤,叫做‘同寺弄里一样’。” 可以说,故乡石门湾,一直是这位艺术家心中的一方净土。一再地吸引着他去回忆这块土地上的人事故物,阿庆、元帅菩萨、四轩注等,丰子恺多次撰文描述。
抗战时期,丰子恺率全家老小逃难到广西、四川重庆等地,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但唯一想起来感到温馨的就是故乡“石门湾”这个名字;做的最温馨的夜梦,就是在故乡“石门湾”的生活。1939年9月6日,丰子恺写就了一篇长文《辞缘缘堂》,其中一句“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
有时逃难途中住在酷热少雨的地方,丰子恺先生便立刻就怀念起朝思暮想的石门湾来,说:“石门湾到处有河水调剂,即使天热,也热得缓和而气爽,不致闷人。”恨不得立刻奔到运河边的石门湾,享受石门湾这温润和清凉。
作为我来说,最喜欢的是丰子恺的漫画,他的漫画很多是从画古诗词意境开始的,把最耐人寻味的景象凝固了,定格下来;国画的笔调,百态的人生,干净的构图,简洁的线条间境界全出,意境旷远。给人以细细的、长久的回味,有着典雅的意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丰子恺的画风雍容恬静,朴实率性,文笔如行云流水,搭配漫画恰如其分,被誉为“随笔大师”。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这些生活中琐屑的事物,通常为人所忽视,但经由丰子恺的笔触呈现出来,加上简短的文字,让读者对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也能一一玩味与省思。
丰子恺提倡“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的艺术观。读他的画,会感觉到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美就在我们身边,它给人以生活的希望和情趣。
四、罗家角遗址
从石门沿桐石公路前行,在石门镇区东北方向2公里多的的地方,公路边有一块指向左转的蓝色指示牌,上面写着“石门罗家角遗址”。沿着乡间小路,转弯抹角,走过一片绿色的田野,前面有一个低低的土岗,上竖一块石碑,标着“罗家角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举目远望,这里与其他江南乡村没有什么两样。其实,这绝不是一块平常的土地,因为我在这里触摸到了中华文明的本源。
罗家角遗址的发现,在中华文明史上意义非同一般。它告诉我们,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今天石门的罗家角一带,就有先民种植水稻,饲养家畜,营建木构房屋,在这里繁衍生息。
当我踏上罗家角遗址,忽然感到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只觉得自己的那一双脚似乎是踩在了历史文化的脊背上,有一种特有的沉重感、苍凉感。我在它的周围一步步地走着,步子是那样的小心翼翼,以防损坏了它那厚重的历史文化。我的一双饥渴的眼凝视着它,我从那一片寂寞的古遗址上,仿佛走到了它的漫长岁月,也走到了罗家角遗址文化的根基。
据介绍,在1956年,当地农民在水田中挖出大批兽骨、陶片和镌刻精美的猪獠牙饰品。文物部门调查发现,这是浙江迄今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12万平方米。为保护性发掘地下文物,省文物部门组织考古队对罗家角遗址进行局部发掘。发掘面积1338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20—350厘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包涵物十分丰富。经碳─14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6905±155年,属马家浜文化类型,处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共发现完整或可复原的石、骨、木、陶器等794件。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的石、骨、木陶器物有794件。第三、四层中的稻谷,经鉴定属于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第四层中的建筑木构件,多有榫卯和企口等残迹。
遗址出土了大批文物,石器有石斧、石锛、石纺轮等,陶器有釜、盆、盘、钵、豆、鼎、碗、壶、纺轮等,骨器中有骨耜、骨哨。在陶片中有少量精美白陶,不亚于商代的白陶,有的白陶片上有乌头纹,还有捏塑男性陶人像。木器中有二件拖泥板状的木器和残存木桨,还有一批加工方正的榫铆建筑构件。
马家浜文化陶器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四片白陶片。白陶是瓷器的先祖,据当今科学分析,制作白陶的原料主要是高岭土,高岭土铁含量低而铝含量高,较红、灰陶耐得起高温,烧成后外型洁白美观,坚硬耐用,人们对高岭土的认识和使用,为后来瓷器的发明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家浜文化的白陶比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白陶早了1500多年。
从制作工艺和焙制方法上看,陶器制作一般都由手工捏制,泥条盘筑,轮盘旋制逐步发展的,焙制方式的演变则更加漫长,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把制好的陶坯堆放在一起,四周围上柴火烧制,但温度不高,难以焙制大的器皿。后来发展为炉灶式,逐步形成陶窑。罗家角白陶的制作工艺应是轮制,否则不会这样光滑、均匀。焙制方法可能是用炉灶式,因篝火式达不到1000度以上。
在罗家角遗址第三、四层中出土的156粒稻谷,经科学鉴定是距今7040年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年代还要早300多年,从而使嘉兴市境成为是迄今所知中国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世界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罗家角遗址还发现了不少陶纺轮,专家考证是“马家浜人”用于纺织的工具。在罗家角遗址出土了这类纺织品实物,草鞋山出土的三块炭化了的纺织品残片,经纬分明,经过科学分析,这种织物用的原料是野生葛,纬线起花的罗纹编织,表明当时的编织工艺具有了相当的水平。作为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织物标本之一,证明了'马家浜人'不再是赤身裸体,披着兽皮树叶,而是穿上了衣服。罗家角3---1层发现的遗物中,还有陶网坠等捕鱼工具,证实了马家浜文化在家畜饲养、捕鱼方式上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眼前的罗家角遗址,依然宁静而又低调地躺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耕之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或是悲情忧伤,或是大喜大悲,或是大起大落,象那一幕幕电影一样,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很久很久的从前,我真为我们的先民感到骄傲。
五、石门湾的桂花
到了石门湾桂花村是一定要去的,因为到了桂花村不仅可以欣赏桂林,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石门湾佳肴。来到桂花村,只见这里到处都是桂花树,在面积不足250亩的小村里,竟种植了近万枝桂花树,其中有市级文物保护的百年以上的古桂花三棵,最古老的桂花树已有140多岁。
品种有金桂、银桂、丹桂等。在圆洞门的一块大石头上,刻着“月宫留香”四个大字。走进门只见桂花树种得密密麻麻。传说当年乾隆下江南时,恰值中秋,正是桂花吐艳之际,龙船一过石门湾,一股幽香扑面而来,船越往南开,香味越浓,乾隆急命停船靠岸,循香而来,在桂林中大饮桂花酒,久久不肯回去,后来命人在石门建立营盘,每次南巡必到桂花村一游。
置身于桂花林中,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没有世事的纷争。如果金秋时节来到这里,你会看到树枝挨着树枝树枝上开满金黄色的桂花。人走在桂树丛里,仿拂进入了桂花的森林王国。在整个空气里到处散发出浓烈的桂花香味,让人陶醉在桂花之中。
因了乾隆皇帝的关系,石门桂花村的名气大增。每年,石门都要举办旅游节,桐乡远近的游客蜂拥而至。据说已经有商家打算做一桌“桂花宴”,里边的菜肴包括桂花鱼、桂花蛋、桂花鸡、桂花三鲜、桂花豆腐、桂花羹,点心有桂花糕、桂花圆子、桂花八宝饭、桂花八宝粥。当然更少不了请客人喝一点吴刚酿的桂花酒,让喝多的朋友,用桂花口香糖、桂花蜜来醒酒。
游客还可以坐在桂花树下,喝一杯桂花茶或者桂花饮料,放松心情,优哉游哉。当然,这里的人们已经把年糕和桂花香结合,推出了一道经典的石门湾美味,那就是桂花年糕。据说这里的桂花年糕入口清香,甜而不腻、糯而不黏,吃后齿颊留香,让人久久回味。我就买了几块尝一尝,那新出炉的又软又糯的桂花糖年糕,甜味适中,桂花香气很浓,真的很好吃。
在我看来,石门实在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江南水乡古镇,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这不仅是乾隆皇帝,以及在石门出生的丰子恺先生的切身感悟,相信也是每一位去过石门的人都会给出的评价。那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一种美好恬淡的生活气息,它如桂花香一般,久久弥漫。
2019-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