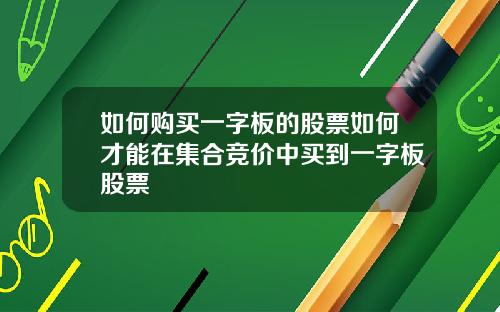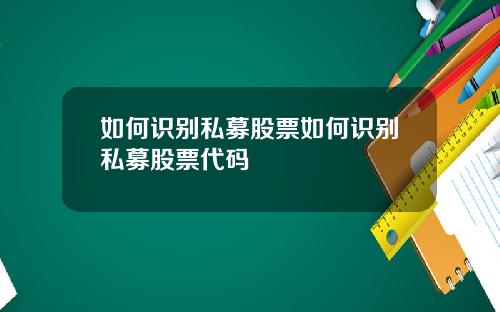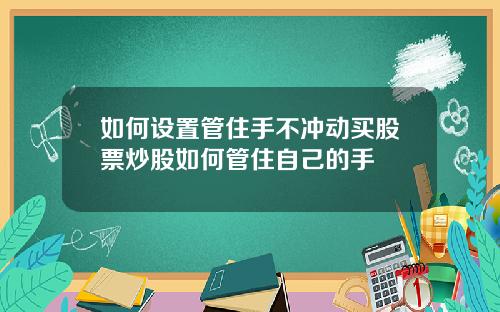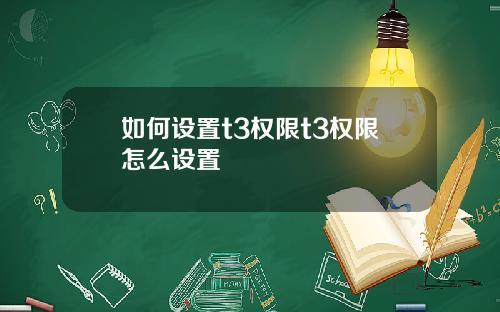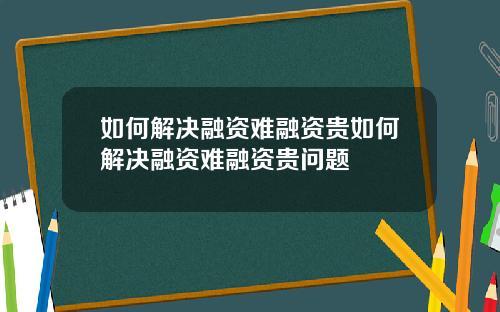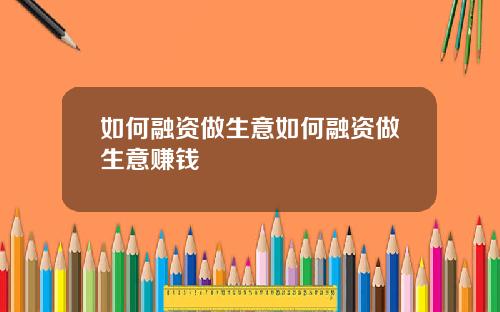磐石铝厂规划
文章目录:
1、验收门窗最容易忽略的六大问题2、「山西画报·太行古堡专题系列」沁水西文兴村:柳氏民居美名扬3、宗璞与《人民文学》的两个三十年
验收门窗最容易忽略的六大问题
对于业主来讲,收房包括的事情很多,业主收房验房中门窗的验收在验房时很容易被忽略,这就导致后期门窗问题频发。从业多年的验房师告诉你,验收门窗时以下六点一定要注意。
设计
门窗尺寸不合规格
门窗一旦安装上后期整改就特别费事,所以必须一次到位的设计好。门窗的尺寸在《住宅设计规范》中是有严格要求的,而一些黑心开发商在建造路磐石为了省下一些花费而随意减小门洞的尺寸,给住户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不便。例如李先生新买了一个房子,装修时却发现门洞过窄,一些大件的家具、材料搬不进去,一测才知道门洞只有76cm,比国家规定的最小的门洞宽度90cm窄14cm。
验房师提醒:验房时业主需要自带一把卷尺,测量一下每个房间的门洞、窗户的尺寸,看看是否符合《住房设计规范》的要求。
门窗尺寸不合规格
门窗验收应注意的相关细节
门窗底框无泄水口
专业验房师提出门窗设计除了尺寸问题外还有另一个突出问题——没有泄水口。泄水口能够使雨天存留在门框、窗框下的积水顺利排出去,不会形成积水,从而腐蚀门框、窗框。
验房师提醒:这个问题需要业主非常细心的去观察每个门窗,否则一旦施工结束,就无从下手了。
门窗底框无泄水口
施工
窗顶无滴水线
门窗的施工是由一些特殊的施工要求的,例如窗户外沿需要做滴水线,防止雨天雨水沿床沿流进窗内或渗水室内墙面,这样会导致室内墙面潮湿,长此以往墙面会长霉发毛。
验房师提醒:门窗渗漏问题是家居生活的一大难题,业主在验房时一定要仔细检查窗户外沿有没有做滴水线,若没有要求施工方返工。
窗顶无滴水线
门窗框与墙体间漏打密封胶
门窗安装完毕需要打胶,这是一个基本的施工规范,若是门窗与轻体连接处没有打胶密封,那么门窗不仅会透风,还会在雨天渗水。
验房师提醒:这个问题不可小觑,业主在验房时要细细观察每个门窗框是否打胶,是否有遗漏的地方,否则等入住在发现问题就晚了。
门窗框与墙体间漏打密封胶
安装
窗扇下框没有安装安全玻璃
对于家装的玻璃使用安全国家也有明文规定,玻璃底边离最终装修面小于50cm的玻璃必须使用安全玻璃。但在现今飘窗盛行的时代,许多人家却忽视了这个规定,为家居生活埋下隐患。
验房师提醒:若是安装了飘窗却没在下方固定扇玻璃的地方看见3C标识,那么你需要找到开发商或是施工方,让他们出具证明,若证明不了安全玻璃,那么可要求开发商更换。
门窗变形
门窗变形多是安装过程中出现磕碰而导致的,例如门窗框被磕凹或是出现划痕,这些问题小则影响美观,大则导致门窗开关卡顿。
验房师提醒:门窗微变形也要整修,否则长时间的使用会加重变形,导致使用不便甚至引发安全问题。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
「山西画报·太行古堡专题系列」沁水西文兴村:柳氏民居美名扬
特别声明:本文为新华网客户端新媒体平台“新华号”账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华号的立场及观点。新华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为提高全社会对太行古堡申遗工作的认识,形成人人参与申遗的浓厚氛围,让更多人认识太行古堡、了解太行古堡,提升太行古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太行古堡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呐喊助威。山西画报晋城记者站联合晋城市太行古堡研究院推出太行古堡专题系列报道,深度挖掘古堡背后的文化内涵,全方位介绍太行古堡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将太行古堡作为晋城“代言人”展现在世人面前。(山西画报·太行头条)
沁水西文兴村:柳氏民居美名扬
柳氏民居
在沁水县寻访古村古堡前,记者照例与熟悉当地古村古堡情况的人商量寻访的路线以寻求较好的建议,他们都极力推荐我们先去西文兴村的柳氏民居,言语中带着诸多自豪感。近些年,西文兴村以柳氏民居这个名称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旅游开发。记者也有些耳闻,在“记住乡愁”这个说法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的今天,一个已经得到修复和开发的古村落很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
魁星阁
名门望族
西文兴村位于我省晋城市沁水县土沃乡。在进行文物修缮和旅游开发之前,村内除几户杂姓之外,九成以上的居民都姓柳,可见西文兴村是一个柳氏家族的血缘村落。据《柳氏族谱》记载:“柳氏出鲁,居河东,世代同居......唐末始祖遵训自河东迁沁历......永乐居沁文兴。吾族世居沁历文兴,子孙耒读发迹,勿忘河东,每逢三坛祭祀,合族报本.....”
柳氏民居全景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柳氏家族最早居住在河东,即今天的运城永济市。柳氏家族是书香世家,到唐朝时家业尤为兴盛,此时家族不但人丁兴旺,还出了一位文人贤士,这便是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一生所著诗文作品达600余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有学者认为,柳氏家族正是遵照了柳宗元的遗训,于明代永乐年间从河东迁至沁水的,可见沁水的柳氏家族与柳宗元同属一个氏族。从明代永乐年间至今,柳氏家族在西文兴村定居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
公共建筑
柳氏民居全景
记者来探访的时候,这个建于明代的古村落经过多年的旅游开发后,不但游人如织,还兴建了停车场等附属设施。进村之后,可以看到古建筑全部被修缮一新。与我省的不少古村落不同,西文兴村占地面积并不大,但这个占地面积只有30余亩的古村落,却先后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名单,成为“双料国村”,村内的古建筑还以“柳氏民居”的名义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双料国村”在我省并不罕见,但村内所有的建筑还同时被列为“国保”,这样的村落数量并不多,足见西文兴村古建筑的价值。
西文兴村虽然规模不大,但作为典型的山西传统村落,建筑类型却相当全,有寺庙、祠堂、民居、楼阁、牌坊等,这些建筑元素一起构成了一个古建筑群。
关帝庙正殿
不算新修的仿古检票处,进村之后的第一座建筑,便是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关帝庙。关公与柳氏世祖都是河东人,所以关帝庙成为西文兴村的王庙,并被建在村口最显要的位置,也是情理之中。关帝庙始建时间无从考证,从明万历年间所立的《重修关王庙碑记》中的记载可以得知,关帝庙于“嘉靖乙未春三月至秋九月厥工告成”,即重建于1559年,其始建年代应当更早。关帝庙在清代又经过了几次重修,但至今依然保持着明代风格和结构。
关帝庙
关帝庙有一进院落,东西宽19.8米,南北长25.5米,内部中央为庭院,四面有建筑合围成四合院,庙门设在东南角。大殿为单檐悬山顶,面阔三间。斗栱上的彩绘至今清晰可见,屋顶为琉璃瓦,吻兽和脊兽都非常精美,应属明清原物。大殿南侧为戏台,可见关帝庙不仅是祭祀场所,还是村内的公共性建筑,是百姓们的公共活动中心。
文昌阁
关帝庙北侧相邻的是文昌阁,同样从碑记中可以得知,文昌阁重修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始建年代依旧不详。文昌阁是一座楼阁形式的建筑,上部为悬山屋顶楼阁,下部为门洞,从门洞可通往村内民居和牌坊,可见文昌阁作为过街楼阁,是从村口进入村内的交通要塞。
柳氏宗祠及柳宗元像
此外,西文兴村的公共建筑还有同样建在村口的柳氏宗祠,但原建筑早已被毁,现存的建筑是古村落开发之后重建而成。
罕见的牌坊街
牌坊街
从文昌阁进入村中心后,首先到达的是牌坊街。牌坊街因为有两座石牌坊而得名。古牌坊作为中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元素,在中国,保存有牌坊的古村落并不少见,拥有比邻而建的两座古牌坊的古村落,并不多见。西文兴村的两座牌坊全部为石料筑造,为“丹桂传芳”牌坊和“青云接武”牌坊,分别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和二十九年(1550年)。两座牌坊属纪念性质,是当时的政府为表彰柳氏族人柳騄和柳遇春这两位乡进士所建。石牌坊为仿木结构,斗栱、瓦当、滴水、屋脊、吻兽等构件均保存完好。
民居建筑
永庆门
我省现存的古镇古村中,能被列为国家级或省级名村的,除了村内有大型庙宇建筑群之外,基本上都保存有几处大型宅院,由于宅院主人都是当时较为富有或官位较高人士,院落都十分高大精美,加上保存相对完好,成为村镇古建筑的代表。西文兴村以“柳氏民居”而闻名,可见村内民居建筑的价值。
司马第院
村内最有代表性的古民居当属始建于明代、重修于清代的司马第,不等你走近,高大精美的院门就足以对任何一个参观者造成震撼。这座院门上有多达9层的斗栱,且是清代原物,这不仅在山西古建筑中少见,在中国传统民居里,也属精品之作。整个院落长51.3米、宽23.3米,正房、厢房、倒座均保存完好,檐廊、栏杆、门窗都刻有花纹,使整座院落显得既规整又精美。“司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官职,“司马第”之名,是为了纪念柳氏家族中入朝为官者所起。
中宪第
另一座较有代表性的古民居为中宪第,为“中宪大夫”柳春芳的府第,建于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西长46米、南北宽23米,为前后两座四合院相连的大型住宅。两座院落组成了两个大小相等且具有鲜明山西特色的“四大八小”型四合院,房屋构件上的石雕和木雕也都十分精美。
堂构攸诏古院天罗地网
此外,柳氏民居古建筑群中,还有“盘石常安”院落和“香泛柳下”院落,这两座院落建造时间均为明代,为村内建造时间较早的古建筑。
耕读书香
方元换字
记者来之前在图书馆读了楼庆西先生所著的《西文兴村》一书。该书出版于2003年,书中村落古建筑的照片拍摄时间还都是修缮之前,照片里的古民居虽然有的已经破落,却可以看到好多人家门上贴着春联,阳台上排列着生活用品,院里角落里摆放着桌椅,可见当时村内还是有很多百姓在居住着,让沧桑的古建筑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魁星阁楼
记者离开西文兴村的时候,村口处的大爷正在手持移动设备听戏,看到记者在注视他,还冲记者憨厚地一笑,铿锵有力的山西梆子在宁静的古村落里更显得嘹亮悦耳。
柳氏民居
行邀天宠古院门头
魁星阁楼
柳氏民居
堂构攸诏古院天罗地网
柳氏民居司马第楼栏、窗花
精品木雕
柳氏民居中宪第鱼身龙头
柳氏民居石雕
出人头地
来源:山西画报晋城号
编辑:董雅连 闫花花
宗璞与《人民文学》的两个三十年
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宗璞的短篇《红豆》,这篇作家的代表作,早已成为经典。时间来到1987年,当时还取作《双城鸿雪纪》的第一卷《南渡记》,以《方壶流萤》和《泪洒方壶》两个中篇的形式,连续在《人民文学》第5期和第6期刊出第一章,鸣响了四卷本鸿篇巨制的前奏。及至2017年年末,《野葫芦引》的收官之作《北归记》,头题刊发于《人民文学》第12期。整整两个三十年,《人民文学》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宗璞先生创作生涯中三个里程碑式的节点。
俄裔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以刺猬和狐狸作喻,将作家的艺术人格和思想人格分为两类:一类是向心的体系化的刺猬人格,一类是离心的多目的的狐狸人格。通观宗璞的创作,似乎趋于刺猬一类。但不论是人格状态,还是文章的气韵,刺猬说之于宗璞终究不够准确,只能说是隔靴搔痒。在我看来,宗璞的创作不妨说是一种植物式的写作。
植物式写作既不同于狐狸式写作,它没有过于分散的目标和诡谲的行动策略,也异于把复杂的世界压缩成简单的程式,把创作变成纯粹利己的以守为攻的刺猬式写作,这两种动物式的写作风格都过于躁动不安。植物式的写作,生长自然是其诉求,但慢一点,再慢一点,并无不妥,三十年或许刚刚好。它跟动物式写作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维持在一种舒缓自适的状态里,既不具备攻击性,也不需要防御能力,它是逐渐呈递,只管生长,因此显得温婉、绵延、朴素,但又倔强、昂扬、苦心孤诣。这样的创作注定是一遭漫漫的生长过程。它反复掂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思考事件和时势之间的种种偶然和必然,就像植物关注气温、泥土的湿度和光线强度等长时段缓慢变化的客观环境,而非一时的交配和掠食。它也不是那类十八世纪或仿十八世纪的矿物式写作,将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全部灌注在故事细节的纹理当中,文本刚一问世,旋即成为化石标本。宗璞的创作,靠氤氲其间的感情取胜,而不是靠剧情的曲折取胜(动物式写作),也不是靠价值导向取胜(矿物式写作)。它在生活的景深中长出藏含历史信息的枝叶,在历史的脉络里绽出生活繁复的花蕾。
因此在宗璞漫长的创作生涯里,小说不是标榜时间在流动、风尚在更替的文学变形记,而恰恰是要证明某种在行进过程中不变的永恒,那躺在河床里的磐石。翻开《人民文学》飘荡着年代感的历史卷宗,宗璞不同时期写下的文字,却并没有给人明显的断裂感,三十年复三十年,在宗璞这里仿佛不过朝夕。以至于我竟有些笃信,在宗璞的小说里,可以鉴别字画年代的碳同位素是失效的,她的小说拥有某种能够抹除年代感的东方神秘力量。它取缔了我们常常自我灌输的时间的效力,让文字具备了超越时空的内通性。两个三十年,能够带走的东西太多太多,但读罢宗璞的小说,我们会更关注当中始终带不走的东西究竟为何。那些带得走的,反倒不值一提。这也是宗璞跟绝大多数的创作者大相径庭的地方,她似乎在告诉我们,坚持未必没有出路,既是南渡,终要北归。
在竞相浓妆艳抹的文学氛围下,宗璞的小说,冷静地暗示了“化妆品”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至于说文学本该有的状态,容光焕发耶?人老珠黄耶?皆归于一句顺势而动。自然的可贵,就在于不逃避,不躲闪,在于那份径直迎上去的果决和从容。也因此,宗璞的小说轻而易举地避免了虚胖、油腻和衰朽、涣散等文学“中老年化”的通病,时隔一甲子仍旧鲜嫩多汁,甚至依然保有一股文气上的青涩和活力。
足可按图索骥的贴身事件与时刻警戒的叙述间距,个人情感和时代背景的纵横盘错,无所谓遮饰的纯真文心,透过这些接近透明的文本“囊肉”,宗璞小说本质上是在探寻人的归宿问题。理查德·耶茨在《建筑工人》这篇小说里,将小说创作比作建造房子,它需要打好地基,砌好墙,搭好屋顶,但小说这个建筑亟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它的窗户在哪里,光线从哪儿照进来。耶茨告诉我们,光线就是小说的观点,是蕴含的真理,是文本给人的启示。而在宗璞这里,小说窗口的作用更多不再是外部阳光的投射,而是自身向外的探看,是屋内灯光的映射,它是一个出口,而不是一个入口。
在《红豆》里,江玫最终选择了更为宏大的理想,但对齐虹的感情依然藕断丝连,青鸟殷勤为探看,那一抹回望,而非砍瓜切菜般决裂,这是小说至今都叫人回味的一个出口。在《南渡记》的第一章里,出口是战乱降临时的一场婚宴,是短时间内避难前的狼狈和舞照跳的优雅间一时难以矫正的错位。而在《北归记》中,出口是渡劫归来的主人公们在意识到生活有着“永远的结”的前提下,仍未停下寻找人生和家国出路的脚步。辞春前,以为归宿是萌芽,夏至时,以为归宿是盛放,待到秋来,以为落土为安是终点,直到冬去春来日,才意识到归宿不过是一种往复,是永远解不开的循环。人一如植物,在四时变幻却又不外乎此的外部局势中,终于彻悟,顽强地活着,彼此更热烈地爱憎,才是不负生命的最佳方式。宗璞不同时段的文笔风格虽然贯通始终,但格局无疑越来越大,目光越拉越长,生命的涵养一如接天莲叶,越发浩然朗阔,熠熠夺目。
只有一门心思埋首奋笔的人,才能六十年如一日不偏不废地进行着自己的耕耘。我斗胆猜测,宗璞绝不愿以与时俱进之名,把自身的创作变成一台时代先锋号机器,因为她的身上流淌着植物的基因。意识流,魔幻,解构,元叙述,怪诞,黑色幽默,所有的妙招和花招,在宗璞面前都显得过于花哨和轻佻,反倒成了对于自己十分才情的十二分吆喝。宗璞笔下的红豆和野葫芦们,生长出了自己的品格,自己的韵律,拥有独特的文绉绉的野气。只有由内而外探照的人,才具有近乎不竭的一以贯之的能量。某种意义上,宗璞创作的缓慢滋长,让小说具有一种平稳的永动特质。永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文学在宗璞这里,从来就不是闹着玩,从来就是使命之召唤。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文学的时代风尚及其领航者变了又变,宗璞却依然站在那里,站在这个一方面日显边缘化,一方面又日益圣坛化的角落,述说着她还没有讲完的故事。那是她自己的故事,关于前尘,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流徙和归来,关于爱情,关于何以家为,关于今朝之为今朝的昨日。正因此,那也是我们的故事。
宗璞的小说是一项古朴的工艺美学,凭借着挑山工式的恒心,抱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心迹,宗璞六十年的创作实践,理应让那些擅于施展小聪明和一味作秀的作家颜面尽失。每一段文字,都是宗璞文学信仰的信条,在信仰面前,没有比忠贞不贰更令人感佩的品行。宗璞就是这样一个文学的信徒。在她的小说里,这位劳模一般的布道者,东南西北都去开凿一番,她是要凭借她最信赖的文字,去确证自己是一个对信仰无比挚爱的行动派。她躬行了,她做到了,这甚至比做到何等境界更加具有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种类似植物的价值,悄然地生长,但必须要生长,在氮、磷、钾等元素的催发下,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自己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直至砌绿成荫,直至独树一帜。(梁豪)